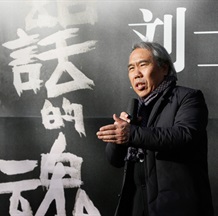诚然,随着新技术的崛起风靡整个世界,“沉浸式”成为了一种语言之外的符号,能够很容易吸引背景各异的观众的目光。但是,在当代语境中,“沉浸式”展览是否仅仅作用于当代艺术并意味着声、光、电的交互技术体验?在不同地域与文化场域中,同样的展览主体是否采用同一种表达方式与叙事手法就足够了?沉浸式展览的归处究竟指向何方?
2019年12月13日,开幕于中央美术学院刘士铭雕塑艺术馆的展览《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刘士铭雕塑艺术展》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沉浸式体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多感官语言上的思考与回应。此次展览作为雕塑家刘士铭先生在国内的回顾性展览,共展出刘士铭先生的作品90余件以及丰富的照片、手稿、草图等文献资料与专题影片若干,其从本质上看更像是一个基于老一辈艺术家个案的、蕴含丰厚学术研究的文献展;然而,取材刘士铭创作中多次表达的窑院意向与沙池布景呈现的第一层展览空间,以及自回旋的脚手架楼梯而进入的第二层空间,共同构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体验,逐步将观者引入“刘士铭的世界”。正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在展览前言中谈到:展览以“‘还原’文化语境的方式将刘士铭的雕塑放在语言’生成’的‘原点’上”,由此呈现了其雕塑“做法”的来龙去脉。
环境:泥巴和土院儿
刘士铭曾说自己就是一个“玩泥巴”的人。“泥巴”是刘士铭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材料,也是解读他人物个性的关键性因素。策展人曹庆晖教授对这一意象的思考从展览题目开始。“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用普通话读来十分拗口,但如若用刘士铭热爱的黄土地上特有的方言调调来读,越读便越有意味。
除了充满着黄土气息的展览题名,颇具特色的窑院儿也是在一层一层的泥浆覆盖下搭建而成。“扳动光景的渡船”、“箍在心头的土院”、“平凡世界的草民”以及“爱屋及乌的情思”等板块分述了刘士铭艺术创作中对渡船、窑院、百姓以及亲情等主题的感想与反思。沉浮于沙海中的渡船陶塑、伫立于砂石中的小巧土院,各式营生与百姓日常都被放置于这样的场景中,直观地反映了扎根于土地中的民生百态。而散落于回旋相连的院儿中的稍大型泥塑作品,更像是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在拐角处遇上的乡里邻居,他们在劳作生活的间歇抬头向观者热情地道一声好。
一处院儿内,刘士铭个人的自叙手稿六篇和照片、文献若干陈列其中,从《回忆我的童年》、《档案·户口·北京》到《我的老伴和女儿、儿子》等,他的一生都在藏在有些难以辨认的字迹中,向观众娓娓道来。一张结婚证、几件小巧精致的泥塑、一段《我和麻雀的故事》的短小录音,一层不大的窑院内充斥着鲜活的烟火气息,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生活情态。
一层展厅深处,一部刘士铭“主演”的“坝坝电影”正在放映,与步入展厅的一小段情景引入式影像形成呼应。而分置在四处的草垛邀请观众落座观展,也意在再现劳动人民的休闲时光场景。一层的东西两侧以剪影的方式表现了在日、月下的不同场景,暗示了一种“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劳动日常。由此,一日的“草民”生活,皆在一层的展厅内徐徐铺开。而刘士铭作为其中一个最为普通的个体,其生活与向往被隐于这样的日常环境中,透过他的作品,与这个时代与环境相互阐释与对话。
声音:陕北调子
如果说再现场景式的视觉氛围烘托只是从视觉语言实现沉浸式体验的第一步,那么音乐的听觉氛围烘托意在进一步将观者引入特定场域。
自搭建在脚手架上的泥土台阶回旋而上,步入展厅二层时,由于天光被大面积遮盖,整个环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暗”。从楼梯口回首,观者能看到置于中心黑色台上的一副双拐和一架三轮车,一束天光自上而下投射其上,在昏暗的二层展厅中烘托出一丝神圣的气氛。双拐与三轮车陪伴着刘士铭走过了人生很长的一段旅程,可以说这两个意向承载着“刘士铭”这一形象的特色与内核。
在二层驻足细听,经由特别采编的音乐自空中飘落而下。极具地方性的陕北调子难以透过词意来清晰传达内容,但来自黄土地的曲调辗转于展厅中而形成的听觉经验,仿佛唤醒了泥塑作品沉睡的魂,在视觉经验的共同作用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与泥土、民众与生活对话的场景得以再现。此时观者若是再次咀嚼“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泥塑上的捏塑痕迹是如何戳动人心,表现地又是何种鲜活的灵魂,似乎都在这层层递进的观展过程中有所交代。
逻辑:从“人”开始讲故事
在策展人语中,曹庆晖教授谈到选用“泥巴”为展览线索时,提出“刘士铭的雕塑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有生活感受’是大家普遍能说出来的一个方面。但像刘士铭这一辈艺术家,哪个不讲究生活深入和体验生活?哪个不懂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为什么刘士铭的这些貌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泥物件、小玩意儿,就更能牵拽和吸引着人们向他、她、它走近而不愿离开呢?”其认为关键性原因或在于刘士铭“生活得更草民,生活姿态更低,更懂得人和人之间、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平等相融、互尊互爱,更需要爱和被爱”[2]。究其根本,刘士铭所处的时代造就了他那一批的艺术家能够透过感知生活而进行艺术表达的普遍性,而刘士铭个人经历与思想追求则使他手下的“小玩意儿”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由此,此展览对刘士铭及其艺术的回顾与解读始于对“其人”的追问。进入展厅,在泥塑的标题之下,记录影像《手》拉开了叙事语境。影片中,画面聚焦刘士铭在泥塑创作中手的状态,还原了其在捏与塑之间,透过作品与生命的直接对话。刘士铭说:“我就是一个做雕塑的人,我得做到死……我想在我的作品中,都有我生命的存在。”以此为楔子,对刘士铭的人生和作品中蕴含的一种朴实诚厚、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品质的讨论得以被展开。
“渡船系列”和“土院系列”是刘士铭的雕塑中极为重要的两个主题,反映的都是底层民众日常劳作与生活的场景;而从小场景的刻画进一步关注到不同个体的情绪,以及家庭关系的温情联结,在“平凡世界的草民”和“爱屋及乌的情思”系列作品中生动体现。
二层中置于中央的双拐与三轮车则是整个叙事脉络的高潮与转折点——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刘士铭常与双拐相伴,三轮则是他往返家和小电窑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说一层的故事从刘士铭其人的性格背景出发,延展至他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观察,那么二层入口处的这两件物件可被视为他一生经历的凝练,亦开启了二层更多元的作品主题。曹庆晖教授曾在艺讯网探班布展时介绍说:“这也是一种’现成品’了。”它们本是陪伴刘士铭生命中最平常的两件东西,甚至现在仍能正常使用,但是在这个展览场域中,它们被赋予了其主人的生命观与精神力,成为了展览叙事的转折与高潮。
在普遍认同的刘士铭的现实主义关注与生活体验之外,展览抓住了“刘士铭其人”这一关键点来构建叙事——他有着更低的生活姿态、他受残疾折磨却热爱生活、他追求自己的内心、他向往爱与被爱。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大家的回顾性展览,“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引入了更为当代的策展理念,在“沉浸式体验”的氛围烘托下,展览强调了刘士铭在“摸爬滚打的生活中习得的’母语’与‘方言’,从而形成了他从生活到语言互为表里的本土经验”[3]。应当说,展览从感官体验与逻辑脉络上都还原了刘士铭艺术语言中的“原点”,由此展开故事脉络,从刘士铭人生经历中重要的物理场域再现与其心灵历程的氛围营造两方面共同完成了展览叙事。
哈莉·吉尔伯特(Hallie Gilbert)曾指出了“沉浸式展览”应该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现实场景的构建以引导观众进入特定时间或是地点的场域;二是创造有别于物理环境再现的心灵体验。[4]如果说物理场域的还原是大多数沉浸式展览着力实现的方面,那么在此之上的心灵体验塑造或许是不同展览应该进一步挖掘的内核。物理场域的构建或许依赖于相似的技术与媒介,然而使一个展览独一无二的关键却在于引发普遍观者的内心共鸣,这种非物理性场域的构建或许在于对展览主体艺术语言的起点与文化语境的追问。以此展览为例,“沉浸式”在作为一种展览形式之外,其基于本土经验差异化与文化语境多样性而延伸出来的可能性或可以被更进一步探讨。
注释:
[1] 参考李曦《沉浸式艺术的起源及发展》,2019。
[2] 摘自《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刘士铭雕塑艺术展》曹庆晖教授策展人语。
[3] 同上。
[4] Gilbert,H., Immersive Exhibitions: What’s the Big Deal?, Visitor Studies Today!, Volume V Issue III, Fall 2002.
现场图/胡思辰